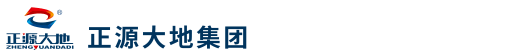马辉——我的母爱
作者:马辉 发布时间:2025-10-30
一、生母到底留给了我什么样母爱
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盘旋了很久很久。尽管时光可以模糊太多东西,却始终抹不去我心里对生母的碎片记忆,那份刻在我生命深处的母爱。我不知道思考过多少次,却始终也不知从何写起。如今父亲和养母都相继离我而去,又逢这深秋时节,总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激发着我,唤起我对两位母亲深深的怀念。我多想把她们的样子永远留住,于是选择用这种方式记录她们给予我的母爱和温柔。
亲生母亲走得太早了,我只能凭借我儿时稚嫩的记忆碎片拼凑她的模样。我记得奶奶在世时常常对我说:“你是你妈妈用生命换来的一条命”;我长大以后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,是因为母亲在患上“肺结核病”的时候,虽然经过住院治疗得到了控制,医生仍严肃叮嘱过母亲五年内不能再生育。当母亲意外怀孕的时候,她与父亲怀着侥幸心理,选择了留下这个生命。这个决定,不仅成为母亲生命的转折,也是我们全家人的人生转折点。
在我很小的时候隐约记得,父亲总是把家里一些好吃的先给母亲,并且告诉我:“你妈妈身体不好,需要补充营养”。我出生的那个年代,农村还是叫“公社、生产队”这样的称呼,因为母亲身体的虚弱没有多少母乳,我出生之后主要靠吃生产队,产仔母牛的牛奶,每次父亲挤回牛奶,都要精心分成两份,一份给母亲滋补身体,一份喂养幼小的我。
命运虽然是残酷的,却仁慈地让我记住了一些珍贵的片段。还记得我大表哥“知青下乡”的那段日子正好住在我们村里,一天下午母亲让刚放学回家的姐姐,带着我去给表哥送饺子。清晰地记得表哥开心地收下了饺子,又把他自己刚做好的糖饼让我们带回来两张。看着我和姐姐兴高采烈地拿着糖饼回来,母亲脸上绽放出温暖的笑容,这件小事像一束光,照亮了母亲善良的品格。
多年以后,我也成了家,有一年,带着女儿和妻子去我四爹家做客,四妈告诉我,亲母在世的时候她总爱来我家住,一住就是好几天,“就像回娘家一样”。这些零星的见证,让我逐渐拼凑出一个待人真诚、温暖的母亲形象。
我永远记得母亲离开的那天早晨,她吃了半个馒头,喝了一点粥,面容慈祥地轻声说:“今天好多了。”但是在上午的时候,父亲坚持要送她去县里的医院。临走时她一直望着我流泪,却不肯上车,而幼小的我懵懂地站在炕上的一角,全然不知这便是永别。这个画面成为我生命中最残忍也最珍贵的记忆,老天爷用这种方式,让幼小的我记住了母亲最后的模样。
生母去世时,我只有四岁。她留给我的不是具体的物件,而是融进血液里的母爱。后来父亲又重新组建了家庭,我自幼就能与四个异姓兄姐和睦相处,能与养母建立深厚的母子感情;可能是亲母在她有限的时间里,用她全部的生命在我心中种下的爱的种子。
如今,我明白了有些爱不需要漫长的时光来证明,短短的四年,足够一个母亲将最珍贵的品质,烙印在孩子的灵魂里。病痛中的她知道自己,是不能抚养儿子长大成人的,所以把她一生最温柔的母爱,浓缩在我最初的时光里,化作我生命中永恒的晨曦。
这份母爱,也许从未离开!
二、妈妈的味道,陪伴一生的母爱
生母离世以后的光阴里,我大多数时间在内蒙古老家跟奶奶在一起生活。奶奶慈祥的关爱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同样是我童年中另一种母爱的延续。记得有一天,奶奶似乎心情很好,对我说:“你以后可以回家了。”年纪尚小的我,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家,只知道回家便能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了。
那是个秋高气爽、风和日丽的日子,我坐着父亲派来的马车,经过弯弯曲曲乡间小路终于回到了家中。那天我家的院子里人很多,热闹得如同过节。我穿过人群,一眼望见了正在与人寒暄的父亲,在父亲身旁有一位中年妇女,她面容端庄和善,嘴角挂着微笑,一边与来往的人们打着招呼,一边在堂屋收拾着什么,那便是我的养母。如今回想,老天爷又一次何其仁慈地将这一幕定格为,我童年最珍贵的记忆之一。就这样我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。我与母亲的情感似乎未曾经历过培养,也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接纳了这份母子的缘分。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叫她“妈妈”,因为我不曾记得有人专门教过我,也不记得有谁告诉我你应该叫她“妈妈”。
父母重组的八口之家,我们一共姊妹六个,我排行最小,有一个异姓的姐姐乳名叫“老三”,其实她仅比我大一个月。记忆中在上小学之前,我们俩一年四季,几乎总是穿着一样的衣服,年幼的我对这件事颇有微词。直到后来才明白,这是父母用心良苦地安排。他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,表达对彼此子女毫无二心的爱。这么大一个重组家庭,可以想象得到父母当初唯有双方付出更多的投入,才能维系家庭的和谐与温暖。小时候我常听到父母讲他们的“真理名言”——俩好搁一好。意思是只有彼此付出真诚爱心,才能有美好地相处,才能成为真正的一家人,用当前流行的话讲:最美好的关系,需要最美好的双向奔赴。
父母常挂在他们嘴边的“真理名言”还有很多,如:记人要记好,将心比心,要想知道打个颠倒,一个巴掌拍不响…等等。他们共同“信服”的这套理念(信服二字也是父母的语言),对我们这种重组家庭的维系是非常重要的;同样这些句子,对我后来的待人处事之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我和“老三”自幼相伴成长,也是童年时的玩伴,她从来没有真正让我称呼过她“三姐”,于是叫她“老三”的习惯延续至今。岁月悄然而逝,转眼我们都长大了。直到某一天我惊讶地发现,我与“老三”之间竟从未发生过争执,甚至连一句口角都未曾有过。这份少见的姊妹关系,是非常弥足珍贵的。我认为这源于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诲。不仅是我和“老三”,还有大姐、二姐、哥也始终与我亲如手足。回想我与兄姐们的关系,可贵之处在于我们互相尊重,彼此以“相待如宾”的方式和睦共处。我认为我们姊妹的融洽关系,对这个重组家庭的维系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兄弟姐妹六人,都是加分项,没有给父母这段本就不容易的婚姻,增添任何一点的麻烦。这可能正是父母的智慧。
记得我哥夏天常到村边的水塘里用网捞鱼,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一起去玩,每当捞回鱼的时候,母亲便会为我们烹制香喷喷的鱼肉,来改善伙食。不懂事的我总是一个人先吃掉了多半条鱼,而“老三”才吃了一点点。母亲却微笑道:“素平爱吃鱼,就让他多吃点”(素平是我的乳名)。还记得小时候我总是因为贪玩,忘记回家吃饭,母亲从不斥责,只是让二姐或“老三”出门把我给找回来。正是母亲的这种做法,进一步增进了我们姐弟的感情。毫无疑问,我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,是父母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。
那时候我老家坝上因为不种小麦,导致白面非常稀缺。每当我生病的时候,母亲总会单独为我擀面条,打鸡蛋卤,成为我小时候记忆中深刻的美食。母亲做的各种饭菜我都毫无例外地喜欢吃,也说不出具体好在哪里,但那种独特的味道,确是唯有母亲才能烹出的感觉。我小时候比较容易感冒,每次都有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,也有母亲“自有的治疗”如刮痧,还有我肚子疼的时候给我按摩,而且非常管用。尤其是母亲的“坝上式刮痧、针灸放血”的医术,即便在我长大以后,每逢回老家感冒时,还常常让母亲做这些治疗。
我在外地成家立业之后,每次回老家,只要一迈进家门,母亲就关心地问我吃饭了没有,累不累,便开始张罗我爱吃的饭。时光飞逝,直到某年的某一天回家,我突然发觉母亲老了,手脚变得有些迟缓了。我心疼地说“妈,以后我回来,您别再专门做饭了”,可她总是默不作声地继续忙碌,而我充满了不忍心。母亲在我心中一直是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,她总是用温柔而坚强的性格,赋予了我深刻而睿智的待人处世之道。
记忆中的每一个大年初一,母亲必定会为全家烙糖饼吃,这个传统习俗从未改变过。2022年春节的时候,母亲已经是八十四岁的高龄了。大年初一那天,我和父母三人在家中,她依然颤颤巍巍地走进厨房,坚持要为我们烙糖饼。我赶紧上前要给她帮忙,母亲说:“不用,你也帮不了”,我心头涌上酸酸的滋味,我不忍心让她为我操劳,又不知道如何替她分担。十一个月后,母亲因感染新冠病毒,永远离开了我。如今,再也尝不到“妈妈的味道”了,然而妈妈用一生倾注的母爱和四十六载的陪伴,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永远不褪色的母爱底色。
三、感恩母爱的丰碑
回首我的人生,或许我是幸运的,我对母爱的理解比一般人更加丰富,母亲不单单只是记忆犹新的思念,更是一座感恩的丰碑、是子女生命中一朵温柔的浪花。曾经几何,我在追忆生母那模糊而飘逸的温柔,总有一种无处安放的渴望,或许那是幼年失恃者必定的心理状态。然而命运总是在捉弄你的同时,又为你安排了另外一种幸运。
养母的温暖与担当,是照亮我人生的另外一束光,养母作为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支柱,她奉献了女性的坚韧与伟大。那种散发着“妈妈味道”才有的饭菜里,看似平常的细小之事,却真正穿透了我童年时光最纯真的成长。我想是养母“一点一点填补了我内心母爱的空缺”,这是一个艰难与不易的过程,妈妈对我来说不仅是养育,更是一种治愈。
生母留给我的是生命和那一抹浓浓的思念,让我自幼便明白失去将意味着什么,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珍惜!而养母给予我的是陪伴和关怀,是用一生诠释的母爱!这两份母爱是无法比较孰轻孰重的,如今的我,对命运给予的安排,早已坦然接受,感恩老天给了我两次母爱,都是我“最珍贵的财富”。
感恩这个深秋,它又一次激荡起我内心深处无限的思绪,让我怀着无比感动的心情,以文字的方式,为两位母亲永远在我心中,树立了爱的丰碑。

亲生母亲

左侧是“老三”,右侧是母亲。

1975年,亲母专程带我去县城的“照相馆”,她亲自为我“设计了动作”的照片。7个月之后亲母去世。

亲母去世后半年,奶奶带我在张家口市,二姑带我去照相馆照的,帽子和上身穿的衣服是二姑给买的,裤子和小背包是二姑亲手为我缝制的。